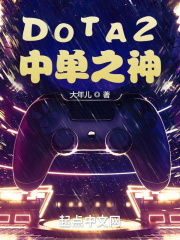三K小说网>佞笔顺 > 8090(第23页)
8090(第23页)
当时他只当是良臣自谦,如今才明白其中血泪。
登基以来,阎涣废除了科举糊名制,亲自督查阅卷,他在殿试时总要问一句,若有良策被埋没,卿当如何?
崔姣姣则在宫中设了女学,收留那些因战乱失怙的才女。
有时夜深人静,她会对着铜灯批改学生的文章,恍惚间,总觉得赵庸之就站在身后摇着羽扇点评。若是他还在世,定是如此的。
坊间流传,帝后二人常微服私访,在酒肆听书生们议论朝政,有人说起前朝科举舞弊的旧事,有位锦衣公子竟当场折断了手中的玉箸。
中元节那晚,崔姣姣在太液池边点燃了一封特殊的书信。
火舌舔舐着宣纸,她轻声念道:
赵先生,李大人,今科放榜,寒门学子占了大半,你们当年的策论,已刻在贡院墙上,再也不会有人抹去你们的才华和姓名。
灰烬随风飘散,有几片落在水面上,像是一只只黑蝴蝶。阎涣默默往火堆里添了一壶酒,那是李澈家乡盛产的梨花白。
当夜,雷雨交加,阎涣破例让人在太庙偏殿摆了酒席。
崔姣姣看着他往地上倾了三杯酒。
一杯敬阎泱,一杯敬赵庸之,一杯敬李澈。
“先生对自己年少落榜之事只字不提,朕却知道,先生一直耿耿于怀。”
阎涣摩挲着酒杯,突然轻笑。
“所以,朕把忠烈祠修在了贡院对面了,望先生能保佑我大夏,代代人才。”
窗外闪电划过,照亮了供桌上并排放着的三样东西,一张染血的皇城地道图,一份被涂改的状元卷,一柄砍到钝刃了的佩剑。
雨声渐密时,崔姣姣听见阎涣低声哼起一首调子,她不知道,那是赵庸之家乡的童谣,唱的是寒窗学子金榜题名的故事。
夜空中,突然划过一颗流星。
崔姣姣仰头望去,仿佛看见三个青衫书生站在云端对她作揖,一个温润如玉,一个眉宇肃穆,一个少年意气。
夏夜的蝉鸣渐渐歇了,寝殿四角的冰鉴还冒着丝丝凉气。
崔姣姣倚在缠枝牡丹的贵妃椅上,看着阎涣*将最后一本奏折合上,长长舒了口气。烛火在他眉骨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那身玄色常服被汗水浸透,贴在脊背上显出紧绷的线条。
“在看什么?”
他突然抬头,眼底还凝着未散的肃杀之气。
崔姣姣踩过地上的织金毯子,足踝上的银铃轻响,挑动着阎涣的心。她伸出手,抚平阎涣紧蹙的眉头,指尖沾了他已冰凉的汗珠。
“看我们这武将出身的陛下,怎么批个折子像要杀人似的。”
阎涣笑着捉住她的手腕,忽然将脸埋进她的掌心。温热的呼吸烫着纹路,他声音传来,有些发闷:
“每每看着你在我身边,就会想起前世那几十年,我独自一人孤独终老的光景,是以我总是夜半惊醒,以为你回来不过是一场美梦。”
窗外一阵风过,石榴树的影子在纱窗上摇晃,像极了当年阎府老槐树的姿态。
崔姣姣感觉掌心微湿,不知是他的汗还是别的什么。这个白日里雷霆手段的帝王,此刻像只被雨淋湿的狼,固执地蜷在她怀里舔舐旧伤。
“笨蛋。”
她将指尖轻插进他散落的发间,安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