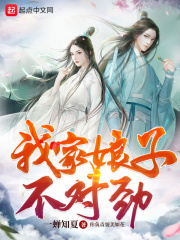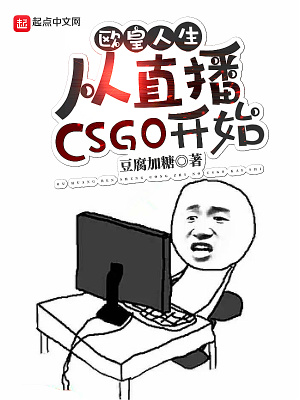三K小说网>大不列颠之影 笔趣阁 > 第二百三十二章 你这是把爵士当成腐败分子了吗(第2页)
第二百三十二章 你这是把爵士当成腐败分子了吗(第2页)
他甚至还当着印刷学徒的面拍胸脯,说自己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跟《英国佬》打官司。
然而他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就在这场官司结束不到半年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结束了他那段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大冒险,重新回到了伦敦。
第一次听说亚瑟想约见自己时,劳埃德根本没把这回事放在心上。
他甚至还特别嘱咐助手:“如果那位亚瑟爵士再提剽窃的事,就告诉他我赢了官司,我合法得很。”
事实上,亚瑟之前也确实没有再找过他的麻烦,直到去年十月,他忽然收到了一张奇怪的信封。
信封里只装着一张随手撕下来的小纸条,上面的句子也很简短:“劳埃德先生,我不喜欢浪费时间。您可以选择继续做一个侥幸的盗版商,前提是上帝依然保佑你。或者,你也可以来白厅街4号找我解开误会,我只等你到下班时间。”
落款写的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警察专员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具体劳埃德有没有单刀赴会,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当天下午,劳埃德的小印刷所来了几个年轻人。等到第二天早上,他就成了《火花》的新主编。
更戏剧性的是,劳埃德加入《火花》之后,不但没有闹脾气,也没有再玩那些下三滥的江湖伎俩。
与之相反,这个原本在舰队街属于“见不得光的边缘人物”的小出版商,在短短三个月内,便让《火花》的面貌焕然一新。
虽然亚瑟在《火花》创刊之初便对它寄予厚望,但说实在的,这主要是亚瑟一厢情愿罢了。
实际上,无论是狄更斯、大仲马和迪斯雷利等《英国佬》台柱子级别的作者,还是整个英国文学圈子,都把《火花》视为低端杂志。但凡有些名气的作家都不乐意给《火花》投稿,倘若不是看在亚瑟的颜面上,狄更斯等人甚至一篇稿子都不想给《火花》投。
正因如此,所有人都想当然得把《火花》当成了《英国佬》和《布莱克伍德》的补位杂志。而质量和市场定位不准,也使得《火花》纵然占据着火车站书报摊的地利,可销量却一直不温不火。
但是在劳埃德接手后,《火花》忽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伦敦城里最懂伦敦市民喜好的文学杂志。
这是整个帝国出版公司和英国文学界都没料到的事情。
毕竟,贵族们喜欢看《布莱克伍德》,中产阶级喜欢看《英国佬》,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喜欢看《经济学人》。
但是纺织厂工人、码头搬运工、鞋匠学徒、铁匠、家庭女佣,他们喜欢看什么?
这件事,还真没多少人研究过。
但劳埃德研究过,而且他比谁都懂。
毕竟,他自己原本就是靠给这些人印一便士盗版书起家的。
于是,《火花》在劳埃德的手下,很快就出现了大量新鲜得冒油的题材。
以舰队街连环杀人恶魔理发师陶德为主角的反派《珍珠项链:一段家常罗曼史》,以法国《巴黎的秘密》为模仿对象的《伦敦秘史》,以及靠打擦边球取胜的《戈黛娃夫人,或,考文垂的窥视者汤姆》,甚至于他仗着有帝国出版和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撑腰,还亲自连载起了《劳埃德政治笑话集》。
并且更令帝国出版的股东们感到欣喜的是,相较于《英国佬》上常常出现的那些知名作者,《火花》的连载作者索要的报酬简直低的可怜。
因为出版业这行虽然看重书籍的质量,但书商们看中质量的初衷还是为了销量,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总是对成名大作家的书籍保持宽容,而对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吹毛求疵。
只要那些正当红的作家有出版意向,那些书商甚至可以在未曾过目的情况下签下订单。乃至于,即便作家尚未动笔,作品仅仅处于构思阶段时,也同样可以出售著作并收取酬金。
因为对于出版商来说,花三四百镑去赌一个小作者一炮打响,反倒不如多出点钱博个稳定收益。
毕竟不是每一家出版社都像亚瑟·黑斯廷斯爵士领导下的帝国出版那样,能够在茫茫人海中慧眼识珠,一眼就分辨出谁是蒙尘的宝珠,谁是一文不值的赔钱货。
不过,虽然出版商一致认为帝国出版代表了业界最高审稿水准,但即便强如他们,也没办法保证百发百中。
尤其是在《火花》创刊的前两年,亚瑟这位英国文学界最大的伯乐在吸纳廉价作者时屡屡走眼,毕竟亚瑟爵士虽然长了前后眼,但在他那个年代,能够继续流传的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可不包括被《约翰牛》大加批判的“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