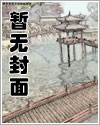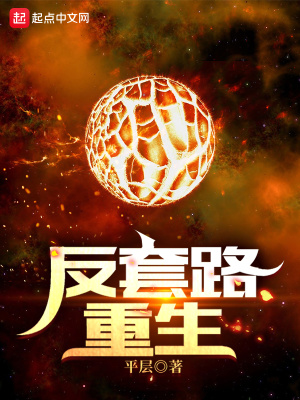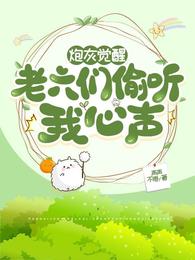三K小说网>全能大画家TXT > 第八百六十六章 艺术的生活(第3页)
第八百六十六章 艺术的生活(第3页)
“我决定要当个专职的画家。就这样吧,这是我的最后决定。”
“另:我把一幅画藏在了远方,你永远也找不到。”
“——卡洛尔。”
这封信通篇写的很简练朴实,结尾处的署名同样也是。
早期的那些信里,卡拉必然有的环节,便是在写给父亲的信里,在结尾处做出尖刻的挖苦。
慢慢的。
那些文字消失了,卡拉的结尾越来越简单,一句礼貌用语,一个名字,或者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字母K。
到了这封信。
则变为了“Carol”。
安娜弯下腰,把这封信很小心很小心的放在了茶几上,动作轻柔细嫩的如同弯下腰,把卡拉的魂灵揽入怀中。
直到抵达命运的终点站,当永恒的寂灭或者天国与来生到来的时候。
力量。
卡拉在旅途中得到的惊人力量,她都始终陪伴着她。
人往往是要经历些什么,目睹些什么,才能获得真正的改变。
可也许踏上旅途的不只卡拉一个人,那些冒险家们和卡拉一样,都曾目睹过相似的场景,为什么卡拉得到了和他们截然不同的视角呢?
这不是“伊莲娜这个姓氏”的魔力。
这是共情的魔力。
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库尔贝、杜米埃……这个咒语的伟力在艺术史上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显现,且从来没有褪色过。
安娜知道,卡拉也不一定能真正的称之为共情。
那是一场极长的旅程,可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之下,亦只是浮光掠影一般的短暂一瞥。
做为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她几乎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中,便真正的在旅程中完完全全的融入四周的风土人情之中。
无论她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出发,这都是客观事实。
带着20000英镑的支票和仆人万事通先生踏上环球旅程的福格先生做不到。
卡拉·冯·伊莲娜小姐同样也做不到。
她带着充足的现金,法朗、英磅,奥斯曼里拉,带着使女和仆人,有支票和手枪,需要的情况之下还会聘请很多护卫。
这些东西一起构成了卡拉身外的那层泡泡,把她和真正的苦难隔绝开来。
卡拉并非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画家。
她是一个印象派的画家。
比起那些真正的融入底层人们真实生活的巡回展览画派画家的画家们,卡拉其实也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