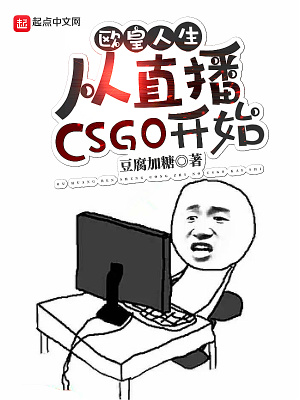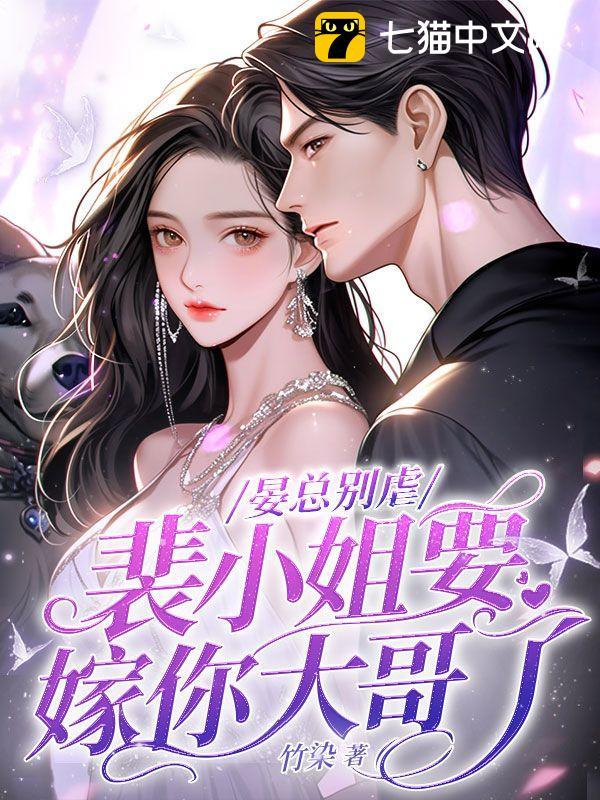三K小说网>七十年代神笔马良闻慈 > 160170(第6页)
160170(第6页)
几位男同志不便发言,乌海青想了半天,提议道:“我们也投报纸反驳回去?”
大家眼前一亮,“好!”
从出版社里出来的乌海青对这事最了解,由他主导,大家删删改改,最后合出来一篇两千多字的稿子,但临到投稿前,却有个新的问题出现。
“我们用谁的名字投稿啊?”
毫无疑问,谁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发声,必然会承受更大非议。
第162章故宫故宫人是社会的产物,他哪怕只是……
人是社会的产物,他哪怕只是求学,也是有家长朋友之类社会关系的。
这种事情往往不是个人的,哪怕非议,近处的也会比纸媒上的更加伤人,毕竟天南海北的陌生人不会把狗血泼到家门口,但你周围认识的人却不一定。
闻慈率先举手:“可以用我的。”
她不在意陌生人的想法,而周围的好友,她有信心对方不会因此对她产生什么意见——如果对方是会随波逐流议论纷纷的人,那对方在最开始,就不会成为她的好朋友。
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没有血缘纽带的牵绊,却是自己亲自筛选出来的
袁韶也坚定地说:“我也可以。”
到最后,除了两个有家有口、家庭格外敏感的同学,剩下五个人的名字都写了上去,乌海青把信纸放进信封,说道:“《首都工人报》我有认识的人,可以投到那儿去。”
大家都没有意见,甚至心里有种被冰雹砸到脑袋的感觉,痛,也痛快。
袁韶笑道:“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
闻慈认同这个观念,并笑着说:“那我们能成为最开始的那个火星,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大家对视一眼,齐齐笑了起来,收起信纸钢笔。为了这封稿子,他们这个周六周日都是泡在画室里的。
10月16日,《首都工人报》刊登了这封稿子。
在敏感的思想形势下,理智者都该选择暂避风头,而这时主动迎接风雨、甚至敢于跳进风暴中的,从客观上来讲,都是一帮天真且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也许不算褒义。
宁姐看到那张报纸,特意来油画班,“谢谢你们帮我说话。”
她最近也收到很多不理解的声音,家人、朋友,甚至是学校里面的同学,她在决定当模特前就预料到了这种风波,但有人维护时,却还是很感动。
袁韶笑着拉住她手臂,“我们也是为了自己——为了艺术。”
宁姐有些担心,“可是已经有人指名道姓地批评你们五个了。”
能考上研究生的这帮学生,往往在入学前就是有些本事的,比如乌海青丞闻,拿过全国性的奖项,闻慈在连环画和绘本那里颇有名气,哪怕其他人,在圈子里也不是无名之辈。
他们公开和批评者对抗,说得夸张点,要是上面注意到,完全是“自毁前途”。
闻慈从画本上抬起头,笑着安慰:“如果这也不敢说,那也不敢画,那我们学习美术是为了什么呢?不如回家照着样板戏去画好了。宁姐,你别担心,我们是很有信心的。”
丞闻不屑道:“现在骂我们的人,都是一些思想守旧的封建之辈!”
有人拍他一下,压低声音,“说什么呢,小心被人听到。”
丞闻不在意,甚至更大声了,“听到就听到,我才不怕。”
宁姐感动又无奈地笑笑,她的担心是好意,但敢署名的这些人,那就不会畏惧结果——在油画班投了稿反对批评者之后,也有许多业内、在野人士,公开为人体艺术发声。
时代已经在前进了,落后在历史车轮后的人,总会有醒悟的一天。
闻慈甚至收藏了这一份报纸,对同学们笑说:“我要把它留作纪念,等到十几年、几十年后,说不准是我们国内美术史的一个节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