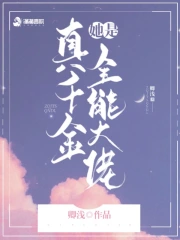三K小说网>七零军婚绝美女配把仇人挫骨扬灰全 > 第880章 真相来临二(第2页)
第880章 真相来临二(第2页)
那天,孙凤英看着女孩沉默地劈柴、喂猪、做饭,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临走时,又塞了五块钱让她去验血。
结果依旧是失望,女孩是b型血。
回程的路上,孙凤英靠在驴车的车板上,眼泪无声地流了一路,陆建国坐在旁边,只能一遍遍地给她递手帕,心里又何尝不是又酸又涩——他既庆幸自己的女儿没受这份苦,又绝望于寻亲的路怎么就这么难。
就在两人快要被失望压垮的时候,鹤南玄托的人带来了消息。
那天傍晚,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找到他们住的小旅馆,递过来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陆同志,京都的苏同志让我把这个给您,说您要找的人,可能在京都。”
报纸是西北当地的《陇原日报》,头版右下角刊登着“地区高考状元王亚男考入京都大学”的消息,旁边配着一张黑白照片。
孙凤英几乎是抢过报纸的,当她看清照片上女孩的脸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眉眼,那鼻梁,那笑起来时嘴角的小梨涡,和自己年轻时放在抽屉里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是她,肯定是她!”
孙凤英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发抖,她抓着陆建国的胳膊,手指几乎要嵌进他的肉里,“老陆,你看,你快看啊!这孩子跟我年轻时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血脉骗不了人,她就是咱们的囡囡!”
陆建国凑过去仔细看,越看心越跳得厉害,照片里的王亚男眼神明亮,带着一股韧劲,确实和妻子年轻时有七分相似。
更让他们激动的是,报纸上写着王亚男考入了京都大学——那是他们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是他们的“主场”。
当天晚上,两人就退了旅馆的房间,连夜去火车站排队买票,硬是在拥挤的售票窗口前站了三个小时,才买到两张第二天清晨回京都的硬座票。
火车颠簸了三十多个小时,两人几乎没合眼。
孙凤英把那张报纸揣在贴身的衣兜里,时不时就拿出来摸一摸,仿佛这样就能离女儿近一点;陆建国则一直在琢磨见面的事,他想起自己在京大有个老朋友吴振华,两人是大学同学,后来吴振华留校当了老师,这么多年一直有联系。
出发前,他特意在火车站的公用电话亭给吴振华打了个电话,简单说了自己要去京大找个人,想请他帮忙。
吴振华很爽快地答应了,说会在学校门口等他们。
火车到站时,天刚蒙蒙亮,京都的空气里还带着初秋的凉意。
两人顾不上回家洗漱换衣服,甚至没来得及喝一口水,就直接背着行李往京大赶。
从火车站到京大,要坐两站公交车,再步行十五分钟。
公交车上,有人忍不住打量他们——陆建国的中山装袖口磨破了,裤腿上沾着沙渍;
孙凤英的头发因为一路的奔波而有些凌乱,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但两人的眼神却异常明亮,像两盏燃着希望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