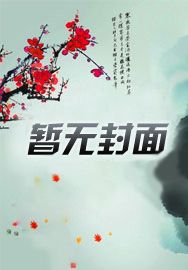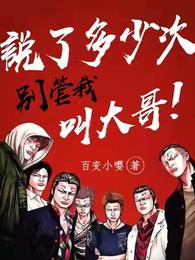三K小说网>寒门首辅顾不易 > 70-80(第14页)
70-80(第14页)
李春华和左喻那边也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帮助,一车车的棉衣跟着风雪一块儿被送到辽东县。每到一车,就能多一车人下田干活儿。
再加上驯马师那边也活动开了,十来个徒弟跟着这十来个驯马师跑前跑后,一会儿跑马一会儿喂草料,也是累的够呛。
全县唯一算得上清闲的人,就只有乌雅连识、摸鱼儿和左晓棠了,三人倒是经常在田埂上碰见。
天空飘雪,落在人温热的肌肤上几乎瞬间就化成了雪水。
乌雅连识看着埋头在田内工作的农人们,看见他们冻红的双手,以及专注的眼神,目光不由颇为复杂。
“摸鱼儿,他们汉人种田,倒也不是很容易,似乎和我们寻找新鲜的草源一样累。”乌雅连识道。
摸鱼儿点点头:“在我们草原上,这么冷的天气都得在手上套个皮子,不然来年手上一定会生冻疮。”
一年种,一年才会长。
但是每到收成的时候,也就是草原异族大举进犯的时候。
乌雅连识抿了抿唇,心里也不觉得当时周稚宁故意让他耕田的行为不对了,反倒是觉得自己有些对不住这些汉人。
正好,旁边就有个正经汉人左晓棠在,乌雅连识便问道:“这个汉人,你知道这些田一年能得多少粮食吗?”
左晓棠迟疑了一下,然后默默摇摇头,道:“回王上的话,在下出身商贾之家,不是农家人,不清楚。”
乌雅连识挑了一下眉头:“难怪本王看你好手好脚的,却没有下去种田,原来你不是农家人。”说完,他就走到农田旁边,稍稍俯下身子看向农田里的农民,“汉人农民,你们一年能赚多少钱?”
那农民是位老人家,向来老实,此时遇见乌雅连识的询问,便赶忙擦了擦手,恭敬地回答:“以前收成好,交税少的时候,一年也能赚个十五两银子。可是现在不行了,一年能赚五两银子便好。”
乌雅连识对中原的银钱没有多大的概念,听完之后他走过去问左晓棠:“喂,汉人商贾,你们一年能赚多少银子?”
左晓棠也听见了那位老人家的话,脸色凝滞了一下。他的长相本来就给人一种呆头呆脑的感觉,如今他摆出这种表情,整个人又透露出一种不知道该如何张嘴的局促感,不由让乌雅连识觉得眼前这人痴傻蠢笨。
乌雅连识啧了一声,看向摸鱼儿:“原来中原也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跟周稚宁一样聪明。”
说完,他便重新走向了农田,去仔细看农田里麦苗的栽种。
左晓棠却依旧呆呆地站在原地,因为他想到了自家的账簿。他虽然不怎么管事,也从未经手过家中的账本,但最起码的银两开销他是算得出来的。
他们左家已经算是米城那边不算富贵的商贾之家了,可早膳还是能做两三桌人的吃食,鲜磨豆浆、鸡汁羹、上好的五香包子、红梗米饭等等,算起来就能有十几二十两银子。午膳又有荔枝鲜鸡、八宝火腿粥、炙烤兔腿。晚膳纵然用的清淡些,也必然有荷叶碧绿粥,再配一叠上好的,从三必居买来的扬州酱菜。
单是这一天,似乎就要吃掉农民好几年的用度。
难怪朝廷规定“士农工商”,且在业的商贾后代不许科举。若是银子叫商贾们赚了,功名也叫商贾们得了,全天下的好事都给商贾了,那整个大明也就乱了套了。
左晓棠觉得自己懂了一点东西,但是死读书过度的脑子还是木着的,有些迷糊。
这时,周稚宁自个儿披着披风打着伞,远远地从县衙处走了过来。看见左晓棠一个人站在雪地里发呆,便走过去拍了他一下,问:“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左晓棠被吓了一跳,看见是周稚宁以后,先是问了礼,然后就说道:“也没想什么。”
话虽是这么说,可嘴唇还是嗫喏着。
周稚宁便揣着手,笑道:“有什么话就说吧,本官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了你不成?”
左晓棠得到了鼓励,便沉思了一下,然后问:“大人,您做官以前是做什么的?”
“本官?”周稚宁停顿了一下,然后道,“本官是寒门出身,未能做官之前,会在闲暇之时去帮家中劈些柴火,或是帮家中的姊妹们运送些绣样去集市里卖。只要是能贴补家用的,本官或多或少都做过一点。”
左晓棠愣了愣,然后才低着头说:“难怪大人此前要问草民是不是一直窝在书斋里读书。”
“怎么?出来转了这几圈,有了感悟了?”周稚宁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