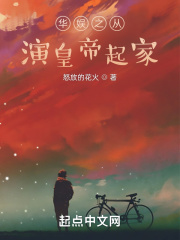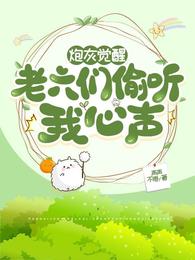三K小说网>顽贼TXT百度 > 第七百五十七章 反差(第2页)
第七百五十七章 反差(第2页)
当然口音这方面的鄙视其实是相互的,在绝大多数元帅军眼中,钱士升这个满嘴官话,时不时加几句吴音鸟语的老头也是少见的怪胎。
甚至就连刘承宗,钱士升都一度认为,其在叛军中脱颖而出,靠的是生员的学识、小官员地主家庭的出身。
因为除了刘承宗这种小秀才,元帅军其他人对钱士升来说,都是过去六十年来未曾接触过的边缘群体。
钱士升有骄傲的资格,大明二百余年,像他这样的状元只有八十个。
他跟元帅军这帮人,本就属于正道与邪路的两个极端,互相看待对方都有极大成见。
而他们的初次见面又确实不够友好,双方的作风都很符合对方的刻板印象——元帅军又凶又蛮,钱士升又刚又直。
但能力和胜利,能扭转一切成见。
钱士升的博学,给元帅军的文盲带来极大震撼。
元帅军的善战,也一样给钱士升带来前所未有的刺激。
当他放下偏见,钱士升就看见了元帅军在亡命徒式凶狠善斗下的另一面。
这支军队绝非亡命之徒,统帅刘承宗甚至没有自己的军劳伴当和厨子仆役。
在战场上,他跟最前线的士兵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向口中塞着炒面粉和肉干,而在驻军时,每天至少有一顿是端着碗下营,随便找个部曲往那一坐,混吃混喝。
反倒是专门从营下给钱士升准备了两个火兵做饭,尽量让他吃上两顿热的。
刘承宗的生活简朴,军队的生活也很艰苦,行军时靠两条腿埋头赶路长途跋涉,必要时人们甚至会在乘骑马骡睡觉,却又很会苦中作乐。
甚至,钱士升很难在那些陕西冷娃脸上感受到他们正在吃苦。
当他转变看法,对这群人了解更深,才知道彬彬有礼的刘承宗,统治并非建立在学识上,而是此人逢战必胜,曾单人砍穿延安府城,在宴会上遭遇刺杀,将刺客直接撞死。
反倒是看上去凶巴巴的张献忠,是个塌实、聪慧、好学的官员,只是生活艰难误入歧途。
当然这其实只是钱阁老摘下一个有色眼镜,而在元帅军战胜歹青后,戴上另一副有色眼镜的结果。
他的聪明脑子,会自动给元帅军这帮人所有行为添加合理性。
就比如张献忠在辽阳,离队半个时辰就让黑烟遍地,杀人放火都被钱士升理解为复仇的极端情况之偶然。
实际上张献忠以及所有跟在刘承宗身边的人,服服帖帖的模样才是偶然。
没有刘承宗,老张出门五分钟砍死八个人,那都叫发挥失常刀带少了。
因为只有刘承宗,能给这些旱灾里失去一切,如同惊恐困兽般的人,提供如同战前,熟悉、安全的环境,抚平伤痕累累的精神,不必再每时每刻直面朝不保夕的绝望恐怖。
说实话,元帅府的人虽然大多是粗人,却让钱士升能感觉到……他比在朝廷更受尊敬。
尽管在统治者这方面,刘承宗跟崇祯非常相似,都不会听从他的谏言。
但两个人的外在表现是不一样的。
崇祯给钱士升的感觉是……无力。
皇上认为钱士升所有建议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大为兴奋,升官赐赏。
但大明的朝堂声音太多,皇上又不够坚定,任何策略无需其他声音,他自己在心里就会质疑。
即使是朝中的有识之士,十分才学也只敢用出三分。
因为任何人提出策略,都会有很清晰的感受:这件事是能做成的,但这件事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