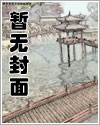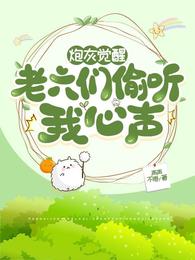三K小说网>静而不争远 > 第545章 追 问(第2页)
第545章 追 问(第2页)
是希雅。她不知何时已来到人群外围,手中牵着他们三岁的小女儿裴慕雅。儿子裴慕希则有些怯生生地躲在妈妈身后,好奇地打量着这群大人。
希雅的出现自带一种沉静的气场。
她走到裴语迟身边,与他并肩而立,目光平静地迎向陆诗文和所有好奇的视线。
裴语迟侧头看她,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有感激,也有隐忧。
“这位记者的问题很深刻。”希雅的声音清晰而柔和,“但答案并不像‘排除’或‘不认同’那么简单。”她轻轻握了握女儿的手,慕雅仰头看着妈妈,大眼睛里满是信赖。
“我和裴先生,对于科技与人类未来的思考,从未停止过交流,甚至争论。”
希雅坦然道,“‘智启未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实验,但它首先是一个‘实验’。语迟作为项目的推动者,他的角色是确保这个实验能够在尽可能安全、公正的框架下进行,为全人类探索可能性。而我和孩子们……”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最终落在陆诗文身上。
“我们的角色,是作为他最后的‘人性锚点’。我们需要站在实验场的‘外面’,保持一份清醒的、未被预设环境完全浸染的视角。当裴语迟沉浸在数据洪流和宏大叙事中时,我需要能够问他:‘今天慕希画画时的心情,AI能真正理解吗?’‘慕雅夜里做的噩梦,数据流能安抚吗?’我们需要提醒他,超越所有的数据和算法,还有无法量化的爱、恐惧、直觉和偶然性。”
她的话让在场许多人陷入沉思。这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制衡。
这时,一直沉默的裴语迟终于开口,声音比之前更加低沉:“陆记者的问题,触及了‘智启未来’最核心的设计哲学。”
他微微停顿,目光掠过希雅,又落回众人,“我们常说,一个实验若无法被观察,就无法被验证;但若观察者本身也被卷入实验系统,观察就可能失真。因此,我们没有简单地将参与者分为‘内部’与‘外部’,而是构建了一个多层嵌套的观察结构。”
他抬手轻点空气,数据柱中的光流随之缓缓旋转,浮现出三重同心环状结构,每一层以不同频率脉动。
“一百位志愿者,生活在我们称之为‘基态层’的空间——这是一个高度拟真的三维社会环境,拥有完整的物理规则、社会互动与情感反馈机制。他们所体验的,是我们为人类未来设计的‘可能性原型’。”
“而我和我的家庭,”他侧身看向希雅与两个孩子,眼神柔和却坚定,“并不在基态层之中,也不在传统意义上的‘控制室’。我们处于一个四维观测层——时间在这里不再是单向流动的变量,而是可被折叠、回溯与并行比对的维度。我们能同时看到基态层中不同时间线上的决策分支,观察同一事件在不同情感参数下的演化路径。但这层空间并非‘上帝视角’,它依然受限于因果律与伦理边界——我们不能干预,只能记录、理解,并在必要时调整实验的底层参数。”
他顿了顿,目光缓缓扫过在场每一位记者。
“而诸位——以及未来通过公开接口接入的全球观察者——你们所处的位置,是五维元观察层。在这里,你们不仅能观看基态层的生活流,也能看到我们四维层的决策日志、伦理评估与情感映射图谱。你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封闭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开放的反思场。你们的质疑、评论、甚至愤怒,都会被匿名化后作为‘外部扰动信号’,输入系统,测试社会结构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