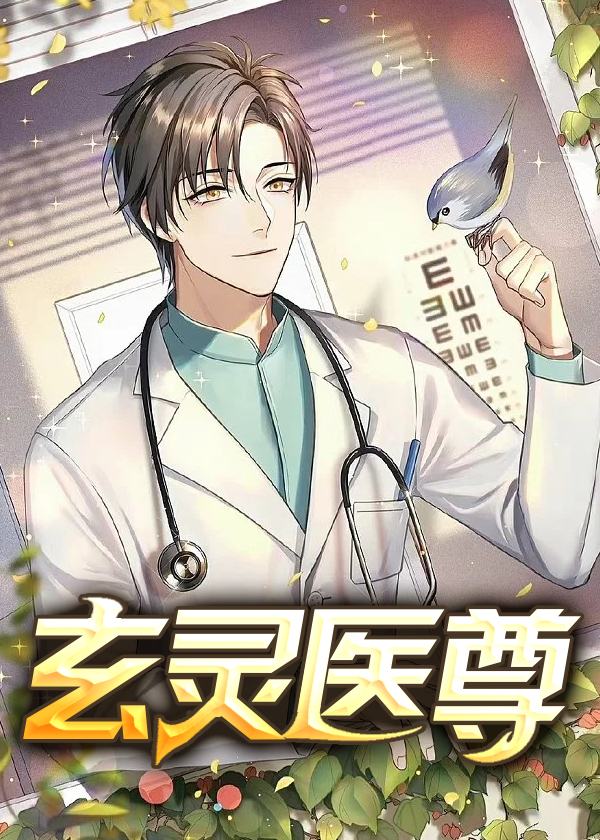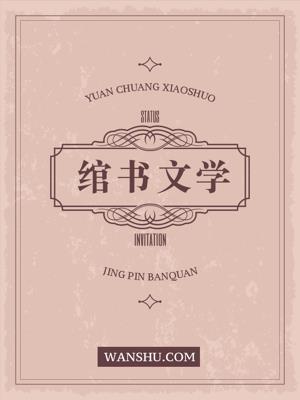三K小说网>穿成小丫鬟后靠美食发家百度 > 3040(第21页)
3040(第21页)
沈砚笑了笑:“我就闲着,想看看前辈们是如何处理一些案子的。”
曹官人方才恍然,连连点头,他瞥了一眼沈砚翻看的那摞卷宗,笑道:“原来如此,那你继续看,若是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问我,那段时间负责整理资料的人就是我——”
曹官人声音渐渐犹豫,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靠去。他迟疑地看向神色严肃的沈砚:“怎,怎么了?”
“曹官人,您是说前几年负责整理并登记报官事宜的人正是您?”
“是啊。”曹官人闻言,点了点头:“那时候我刚刚进大理寺为贴书吏,负责整理记录,这日日从早抄录到晚间,没得片刻清闲。”
曹官人说起那时经历,也是唏嘘不已。他连续数次科举失败,为偿还债务,养家糊口便通过大理寺的甄选,进大理寺为吏。
在寻常百姓眼里,乃至自家亲眷眼中,能为大理寺官吏已是极为体面的事儿,可只有曹官人才晓得一路的艰难。
初入大理寺衙门的小吏,收入与差役没有区别,统统被归为贴书吏,指派给孔目押司做副手,负责抄写各种案件资料并归档。
孔目押司也是不入流的小吏,他们对着官员那是谨小慎微,谄媚取容,对着自己这般新进小吏又是另外一张脸孔,打骂呵斥都是常事。
不止是抄写各种资料,他们还时常得帮忙跑腿,通宵达旦的处理事务。
“竟是有这种事。”沈砚震惊。
“是啊。”曹官人瞥了一眼沈砚,心中暗道:像是沈砚这般的年轻人,本是最容易被老油条欺负的对象,只是还未等人出手,便传出沈砚也是衙内出身的消息来。
衙内出身的人跑来当小吏?
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新型爱好?
不止是曹官人觉得难以置信,回想当时消息传开时诸人的反应,他更是哂笑一声。
曹官人摇摇头,把这些思绪抛到脑后,继续往下说道:“也是我运气好,当时遇见的胡官人甚是好心肠,时常会来帮我们整理一二,还提前让我们走呢。”
“胡官人?哪位胡官人?”
“啊……沈君不认识也正常,毕竟这位胡霖胡大人已调离大理寺五六年了,时下为太府寺左藏库副使。”
“太府寺左藏库副使?”沈砚回忆一番,对这人毫无印象。他心中微动,故作好奇地继续往下询问。
沈砚旁敲侧击几句,曹官人便松了口,说出不少过往旧事来。
待听说胡官人任职的时间与职务,沈砚顿时心头一震:荣小娘祖父母去世时,此人正是大理寺评事,而荣小娘母亲去世时,他又正好是开封府左军巡使。
尤其是后者,更是让沈砚眸色微沉,要知道他未查找到荣娘子死亡时的报官记录,要么是亮哥听信流言,要么便是这桩案子压根没被送到大理寺。
其中道道程序,很难彻底清理,除非出手的人恰好是负责汴京乃至陪都水火盗贼狱讼事务的左军巡使!
若是他得信并亲手操持此案,事后再抹除痕迹,以正常死亡结案,那自然而然不会有卷宗送至大理寺。
沈砚心思急转,面上却是不动声色。他假装翻找卷宗,半响才挑眉看向曹官人:“曹兄莫非是逗我玩?”
“此话怎讲?”曹官人顿时不满。
“你看看。”沈砚翻出不少卷宗,半是抱怨半是疑惑道:“你说胡官人曾帮忙登记造册过,可我翻看了那么多卷宗,都没看到胡官人的记录。”
大理寺的所有卷宗,都要求溯源,也就是说所有经手人都必须签字按押,偏生他翻看的那些记录都是曹官人与另外两名当时为贴书吏的名字和指纹,未见胡官人的签字。
曹官人闻言心头一跳,赶忙竖起手指嘘了一声。他先偷偷往回撇了一眼,见陶应策未关注这边方才放心,压低声音道:“沈君有所不知,胡官人是帮咱们的忙。我们几人那时不过是个小小贴书吏,哪能劳烦胡官人签字登记的,故而……”
沈砚眨眨眼,接话道:“故而胡官人处理完,便把卷宗交予你们,由你们再登记造册?”
曹官人连连点头:“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