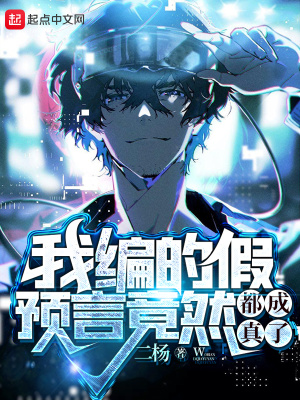三K小说网>大明朱标朱元璋头号黑粉最新章节更新时间表 > 第252章 交情莫逆(第2页)
第252章 交情莫逆(第2页)
“总好过朕还要将相同的话说上个三五遍。”
“那不如臣妾请韩国公暂且回府?”常氏眼眸微挑,温声开口道:“毕竟是国朝老臣,守在宫门外兄长却不召见,有伤朝廷重视老臣之心。”
“不妥。”
“若朕明言不见,亦或是你这位皇后出面劝离韩国公,如此反倒会让朝中官员揣测天家之意。”
朱标深吸口气,继续说道:“今日放粮之事,得知朕有心以朝廷插手民间商贾。”
“朝堂上的官员进言本是应该。”
“倘若此时劝离韩国公,本打算明日一同进言的官员或会心生动摇。”
“到最后若只剩李善长、刘伯温、詹同、高启这些老臣出面,未免显得他们势单力孤。”
“朝中政务若有艰辛,总不能全都着落在这些老臣身上,倘若真是如此,我大明朝堂岂不显得青黄不接?”
被朱标这么一说,常氏一时不太明白,秀眉也不禁微微一皱。
不过常氏却觉得眼下之事有些拧巴。
就朝廷插手民间商贾一事,朱标知道明日朝会定是百官劝谏,此时不见李善长也是不想麻烦两次。
可话说回来。
明明知道明日的朝会上,刘伯温、詹同等官员要一齐劝谏,然而朱标却压根没打算事先打压,甚至还暗中为他们增势。
想来也对。
听闻朝廷插手商贾,正直之臣本该劝谏。
朱标又是铁了心要匡正商贾,同时又不能打击这些正直的忠心。
再有!
朱标也不想看到朝廷有事,独独只有李善长、刘伯温、詹同、高启这些老臣出面。
所以眼下也只有委屈李善长让他一直在宫门外守着。
朝政当真复杂。
或者说,当一个似朱标这般体恤臣下的君王很是辛苦。
毕竟若是换成老爷子,那此时必然是先召李善长、刘伯温入宫训斥一番,省的他们明日朝会带头谏言。
“不过朕倒也有些意外!”
朱标驻足殿内,眺望宫门的方向幽幽说道:“按理来说,李善长那善藏的性子本不该是他今日求见。”
“以他只想安稳残年的想法,眼下该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才是。”
“今日守在宫门口,势要见驾当真有些反常。”
常氏也想不明白这其中道理,此时忧朱标之忧,没有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