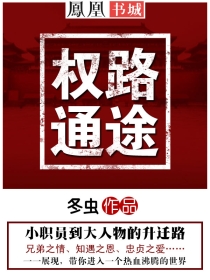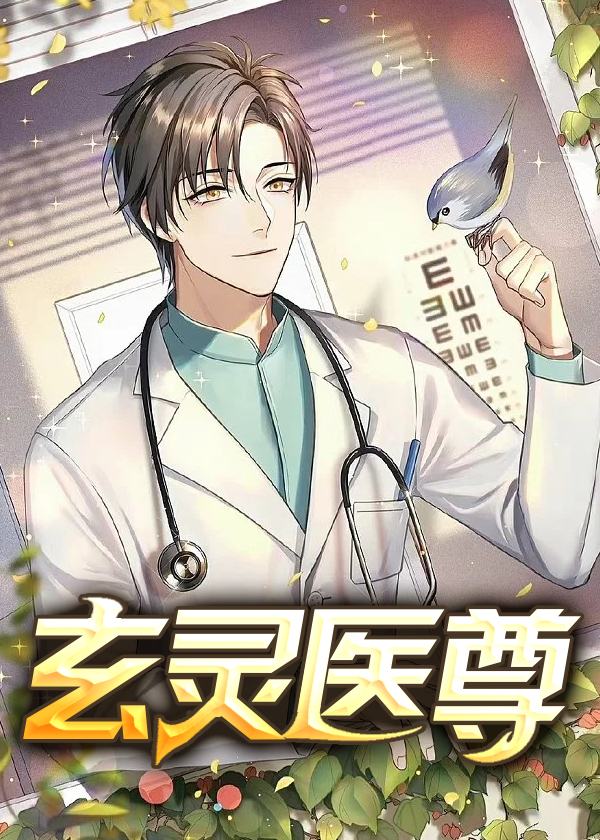三K小说网>华娱从神棍到大娱乐家免费 > 第三百三十三章 刘伊妃 先母曾文秀之墓(第7页)
第三百三十三章 刘伊妃 先母曾文秀之墓(第7页)
张太太取出桂花酒酿元宵摆在餐桌上:“那会子张姑娘也住这屋,半夜打字机咔哒响,吵得我麻将都打错牌哩!“
“刘小姐,一起吃一点吧?”
“不了不了,谢谢!我早晨吃好了过来的。”
张太太热情得很,当即请她坐下,也不忙着自己吃饭,絮絮叨叨地讲起了张纯如当年在这里和慰安妇幸存者的访谈实况。
刘伊妃扶了扶黑框眼镜,一笔一画地开始记叙。
从这个鼻尖嗅着酒酿元宵香气的酷暑早晨,她正式走进这座风雨起苍黄的城市。
晨雾未散的金陵图书馆前,梧桐叶滤下的光斑在石阶上跳跃。
小刘踩着露水踏进特藏室,素色衬衫被窗棂切割成斑马纹。
管理员老周推来移动梯,金属滚轮碾过柚木地板的声响,惊醒了沉睡的尘埃。
“你好刘小姐,剧组打过招呼了,你可以待到中午,暂时没人过来。”
他指着临窗的榆木桌:“这里就大概是当年张女士的座位,她在这里查了一周的资料。”
“谢谢,添麻烦了。”
老周笑着端来一杯雨花茶:“不客气,我是金陵人,说什么都要支持的。”
刘伊妃安静地坐下,微缩胶片机嗡鸣着吐出1937年的《纽约时报》。
她摘下半边口罩,当1937年12月13日的头条浮现时,指尖悬在受难者照片上方三寸,像给旧时光行注目礼。
中午,遇难同胞纪念馆。
刘伊妃蹲坐在万人坑遗址前临摹幸存者证言,鹅卵石小径将牛仔布料的膝头磨出淡青印痕。
她在体验张纯如当年的心绪,不觉间泪水将笔记本上的小楷晕染成水墨痕迹。
纪念馆的白墙将阳光折射成珍珠色,洒在她临摹证词的本子上。
忽有穿中山装的老先生驻杖而立:“姑娘,‘卅’字要这样写——。”
他枯枝般的手在虚空中比划旧式笔顺。
小姑娘抬头,巧笑嫣然:“谢谢伯伯。”
写着写着,泪水突然在“母亲寻子”的段落晕开,将墨迹洇成江心洲的轮廓。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彻底代入了张纯如,还是酷暑炙人,刘伊妃只觉得金陵的一切都那么暖心,即便在这样肃杀的纪念馆中。
下午,浦口火车站。
热浪渐渐散去,蒸汽在月台铁轨上织出薄纱。
刘伊妃立在褪色的“天下为公”标语前,口罩上方露出的丹凤眼让卖糕阿婆看得怔忡。
竹蒸笼揭开的刹那,梅花糕的甜香裹着桂花蜜流淌。
“阿婆,请多撒些松子仁。”
刘伊妃记得张纯如笔记中,初到金陵在火车站下车,就是拿这一样小吃果腹。
她要尝一尝,再带一些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