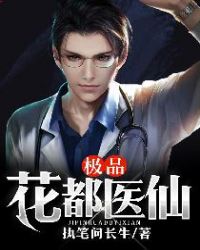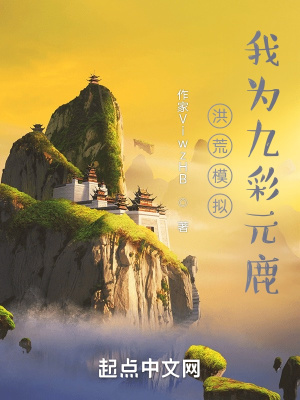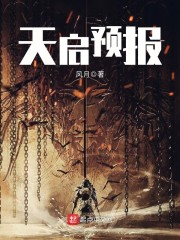三K小说网>都重生了谁还做演员啊洛珞 > 第393章 掌管天气预报的神(第2页)
第393章 掌管天气预报的神(第2页)
这就像是在盘古堆杜瓦容器外围,无声地焊接上了一层更厚、更坚韧的安全冷屏。
一阵低沉的嗡鸣从脚下的结构中隐隐传来,那是重型设备的动静。
洛珞的目光重新聚焦在主屏幕上那不断流动的光点矩阵上。
紧张感是客观存在的,但还是那句话,退出ITER,不过是搬开了挡在技术冲刺跑道上的绊脚石。
而此刻提升的安保,就像为这冲刺加固了跑道护栏——它不是为了限制速度,而是为了保证这最后的冲刺能够不被任何外来的恶意所干扰或打断。
“盘古堆点火必须成功……不只是我,国家也跟着一起押上了所有筹码。”
他无声地对屏幕上的模型宣告,再次挺直脊背,双手放回操作台。
外部世界的压力骤增,却奇异地转化为一种更纯粹的定力。
他仿佛能听到那无形的防护壳悄然合拢的声音,隔绝了所有风暴,让思路更加清晰。
往后的日子里,洛珞几乎完全待在了岛上,力求把自身的风险降到最低,也给负责安保的同志们省了大事,连秦浩和吴峻都少见的各自放了个长假。
唯一辛苦的就是洛珞,半年的时间里没有离岛半步。
三月的黄泽岛,海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吹在脸上像粗糙的砂纸。
岛中央原本的小渔村痕迹已被彻底抹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用混凝土和钢筋编织的几何图案——盘古堆的基座。
验收的日子临近。
工地上弥漫着一种无声的紧张,大型机械暂时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人员拿着精密仪器在各个区域穿梭,记录着微米级的沉降数据、钢筋的应力状态。
洛珞裹着深色的防风外套,身影在清晨的薄雾中显得有些单薄。
他并非例行公事般地走过场,而是真正深入地走在混凝土浇筑的庞大地基上。
他手中的机器连接着遍布基座的传感器网络,实时显示着温度、湿度、应力的三维模型。
大部分区域的数据都呈现出令人满意的绿色光谱。
然而,当他行至靠近海边,海风最为强劲的3A区和7B区结合部时,脚步停住了。
指尖在光滑冰冷的混凝土表面缓缓划过,触感细微的差异让他心中警铃微作。
平板上的模型放大了局部应力图,结合部的数值呈现出一种不易察觉但持续存在的、高于设计平均值的拉伸应力带。
“赵工”
洛珞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现场的轻微嘈杂:
“这里的超声波探伤报告给我看看。”
旁边的赵工程师立刻递上报告:
“洛总,检测过两次了,报告显示无明显缺陷,都在合格范围。”
洛珞接过报告,快速浏览着图表和数据。
数值确实在合格线内,但靠近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