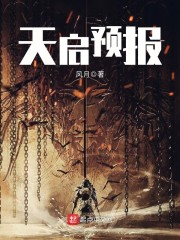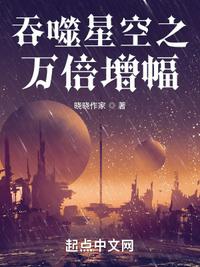三K小说网>全能大画家TXT > 第八百一十一章 小顾子重画老教堂猫大王欲打侦探狗中(第3页)
第八百一十一章 小顾子重画老教堂猫大王欲打侦探狗中(第3页)
树懒先生为顾为经读《小王子》,书里飞行员对小王子说:“沙海之所以那么美,是因为沙漠藏着一口井——只有谁翻过最高的沙丘,你才会相信。”
这话听上去有点抽象。
顾为经一直以来,不是很能理解这句话里的含意。
他在画架前站着画着,渐渐地有了属于顾为经自己的领悟。
美就在那里。
井就在那里。
只有翻过最高的沙丘,只有站在同一片雷雨云之下,同样的云彩之下,虔诚的看过夕阳下燃烧的云海,看着雷雨云中绽放出的闪电,像着女画家卡洛尔那样,以印象派的方式用细腻的笔触和破碎的色块描绘自己的心灵,你才会相信它的存在。
这些方面,顾为经比起以前,更多获得的是“术”的改进。
相比技法上的变强,经历了西河会馆的事件以后,顾为经再次拿起画笔描绘老教堂,比起云彩的动态、光影的明暗、教堂的色泽这些细节上的细微不同。
他获得更多的是“道”的进步。
好的艺术作品,永远隐藏着创作者对心中人文精神的寄托。
照着画了那么多遍老教堂。
笔触、光影、细节这些方面,他以前就做的很不错,比起一些画面动态上的不足,顾为经对创作者情绪的体悟,反而欠缺的更多。
“只有谁翻过最高的沙丘,你才会相信。”
顾为经本质上以前多多少少还是把那幅卡洛尔的作品当成宗教画来形容。
19世纪后半叶。
就在印象派画法在塞纳河畔逐渐成形的年代里,法国巴黎恰好也正在进行一场天主教复兴运动。
那时期不少画家都画过以教堂、宗教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包括信仰不可知论的莫奈,也画了一大堆教堂画。梵·高这种,干脆就直接是传教士出身。
顾为经把《雷雨天的老教堂》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去理解,自然也就染上了同样的思维底色。
这画肯定不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救世主”那样宗教氛围特别特别浓厚的作品。
可教堂本身就带着强烈的象征意味。
顾为经以为,就像莫奈的《鲁昂大教堂》一样,卡洛尔依然把身前的教堂当成“神圣美丽”的象征,只是把关于宗教圣殿在她的笔下,替换为了关于色彩的圣殿。
他以前总是有点在自己的作品之上,还原不出女画家笔下的神圣感。
顾为经一度以为,这搞不好是因为他不是个信徒的原因,文化背景不同,所以他没有办法全部体会卡洛尔把情绪落在画纸上时的想法。
从西河会馆出来以后。
顾为经发现他错了。
他再次回想那幅画,心中意识到,他对卡洛尔心情的体悟还是浅了。
他把自己代入到了十九世纪印象派画家的视角看向老教堂,却代入的还不够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