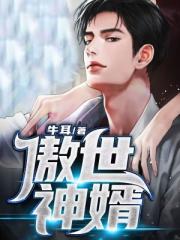三K小说网>朕这一生如履薄冰笔趣阁 > 第515章 上林宴(第3页)
第515章 上林宴(第3页)
因为卫绾,本质上并不是儒家的人。
只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性格,让卫绾本能的对重视、强调秩序的儒家,有天然的好感。
而对于奴隶上告主人这种违反秩序、破坏秩序的突发事件,卫绾也同样有本能的抗拒。
但与窦婴这个假儒将相比,卫绾,却是正儿八经实打实的儒将。
——窦婴这个儒将,重点在‘儒’,‘将’只是顺带。
而卫绾这个儒将,却是行伍出身,以‘将’为主,而‘儒’,则说的是卫绾这个武人的性格。
所以,卫绾对此事的态度,除了本能的,对秩序被破坏感到不满外,也还有武人、政治人物所具备的基本政治敏感度,为卫绾带来的危险感知。
危险源自何处,卫绾说不上来。
只是隐约间,有一个身影告诉卫绾:此次的事件,远不是奴隶告主、以下犯上,破坏秩序这么简单。
甚至关键都不在于奴隶告主!
而是在于奴隶,状告奴隶主的内容,也就是如今声势浩大,已经传遍天下的所谓‘奴籍案’。
故而,对于天子刘荣将朝中公卿重臣,都邀请到博望苑参加宴席的举动,卫绾有疑虑,有迟疑不定,却并未像窦婴那般,脸上明写着‘我要找陛下好好说说’!
与窦婴的激烈反应,以及卫绾的迟疑不定相比,同为三公的大司空韩安国,倒是相对淡定了许多。
首先,不同于窦婴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从小娇生惯养,出道就是太子詹事,吴楚乱起便立刻成为大将军、回来就做了太子太傅,并预定了丞相之位的外戚子弟,以及行伍出身,入仕便是朝臣二千石起步的武人卫绾;
从最底层一点点爬上来,在吴楚之乱爆发后,正儿八经指挥过睢阳保卫战,并在关东郡国有过‘基层履历’的韩安国,即没有窦婴的理想主义,也没有卫绾的天真烂漫。
韩安国很清楚:政治,往往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清澈、干净,更不会有渭泾分明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按照韩安国多年来积攒下的政治经验,政治这个东西,往往就是两方——甚至几方势力,对敌方造成打击、为本方谋其利益的媒介。
而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会争取求同存异,寻找各自的共同目标,达成一致;
在无法达成一致的地方,则通过妥协、让步等方式,来得到一个大家都不很满意,却也都可以勉强捏着鼻子认下的结果。
等事情解决了,大家表面上谈笑风生,和颜悦色,暗地里争权夺利,一切照旧。
好比此次的奴籍案,之所以能迅速扩散开来,并发展到如今这‘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天子刘荣的默许,甚至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而刘荣这么做的目的,也很明显。
——通过此次的奴籍案,来使汉家存在的一部分问题,从原先,大家都心照不宣、看破不说破的幕后,搬到大家都无法再装鸵鸟的台面上。
比如,官员贪腐问题;
比如,地方郡县官商勾结、豪强愈发脱离掌控;
再比如,进一步改善奴隶制度,借机在‘倡导用外族奴隶’一事上,再用力推上一把。
而作为既得利益者,兼刘荣理论上的意志执行者,朝公重臣们对此事的态度,则必然与刘荣的目的有所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