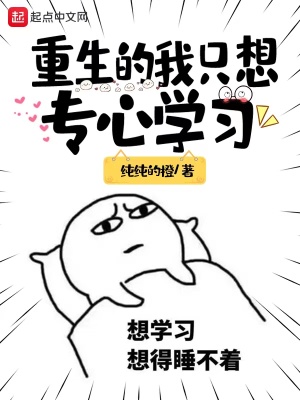三K小说网>剑出人间南朝陈免费阅读 > 19 讨个说法小事大事(第2页)
19 讨个说法小事大事(第2页)
“也罢。”
陈杨氏不再拒绝,家里确实已经揭不开锅了。只是这么一大锭银子在乡上可不好铰开来用,得找大户来兑换成铜钱才行。
至于钱财来历,妇人曾听丈夫说过,陈晋与城中富商王家独子是同窗,因缘际会之下,得了一份不错的报酬。
不管怎么说,手头有了钱,一颗心仿佛有了着落,不再那么惊慌无措。
有钱就有了希望,能吃饱饭,能请到大夫,能买到好药,丈夫的命保住了。
陈杨氏感觉自家侄子变化甚大,以前的他不修边幅,老气沉沉,落魄得很。
可现在呢,简直像换了个人,年轻了许多的样子。
这是好事。
陈晋的沉静和大方,一下子扭转了场面。
堂侄女陈敏走来,仰头看着陈晋:“小郎叔叔,你说我爷爷能活吗?”
陈晋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安慰道:“没事的。”
女孩顿时破涕为笑,跟着奶奶母亲出去,帮忙干活了。
此际陈源醒转,睁开眼睛看到陈晋,忍不住老泪纵横:“小郎,这次的事,是大伯对不住你。”
“哪里的话?”
“哎,我识人不明,糊里糊涂的求人办事,没想到事没办成,还把钱全搭进去了。我悔呀!”
陈晋宽慰道:“大伯,你不要想那么多,安心养伤。”
又说了几句,起身返回自己的东屋,放下书笈,闭目养神。
到了晌午时分,陈志接大夫回来了。
大夫姓“郑”,在茂县正元堂坐诊,善于外伤正骨,要不是陈志舍得花钱,都难以请得他来。
钱花得多,也用得值,郑大夫是个专业的,观察一番后,开始上手接骨,继而用药。
在整个过程中,陈源痛得死去活来,拼命忍住。好在他虽然年过五旬,但身子骨颇为壮实,忍受得住。
等骨头接好,敷上药,便算捡回条命。
“头三月不可妄动,每七天换一次药,半年之后,应该无恙。”
郑大夫洗干净手后,吩咐说道。
陈志连忙道谢,又请他留下用饭。
郑大夫自是应了,等上桌后,发现有肉有鱼,竟十分丰盛,不禁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