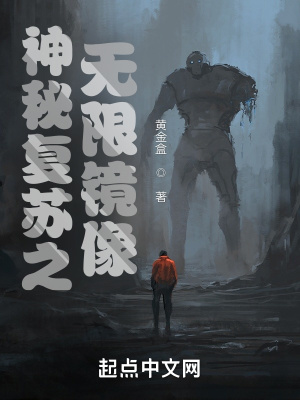三K小说网>剑出人间南朝陈免费阅读 > 17 法器神宝认祖归宗(第2页)
17 法器神宝认祖归宗(第2页)
陈源低声喝道:“阿志,早跟你说过了,不许叫‘赵门子’,被人听见,事情可就办不成了。”
陈志嘀咕道:“可他就是个看门的。”
“哎,你这性子,张口便得罪人。这就是没读成书的结果,不懂礼法人情。看门得分清楚是哪家的门,那可是赵主簿家。若非门子牵线,咱们如何能搭得上赵管家的路子?”
“花那么多钱,就为了见个管家,我觉得不值。”
陈源摇摇头,恨铁不成钢地道:“求人办事,没有脸面人情,就得花钱。”
“可也太多了。”
陈志颇不服气:“光置办这一席,就花了五两银子,都能买一亩良田了。这哪里是吃饭,摆明是吃银子。”
陈源看着他:“阿志,我知道你心里有气,觉得我偏心,只顾着小郎的前途,可谁叫你没有读书的天赋呢?”
陈志分辩道:“爹,今时不同往日,他一直考不上,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陈源哼一声:“所以我才煞费苦心地让小郎进衙门办差,一来为了历练,老话有说‘人情练达即文章’。我认为小郎的才气文采是够的,只欠了份人情通达;二来如果他真得考不上,但能在衙门立足,日后转正过来,同样是晋身之道。”
说到这,顿一顿,问道:“你可还记得咱们陈氏是如何迁徙到大塘乡来的?”
陈志回答:“记得爷爷说过,一百年前,朝代更迭,战乱纷纷。曾祖父落难逃荒,离开了郡城祖地,流落到此,结婚生子,才有了咱们这一脉。”
陈源点点头:“不错。虽然你曾祖父,还有爷爷皆已离世,但祖训犹在,就是要培养个读书人出来,跻身仕途,光宗耀祖,并带领我们返回祖地,进入宗族祠堂,认祖归宗。这个,不但是曾祖他们的夙愿,更是我和你老叔的毕生志愿。”
闻言,陈志默然了。
大塘乡为多姓混居之地,大部分的人家,基本都是在那波战乱时期逃难过来,在此落脚成家的。
人心思旧,总想着落叶归根。
尤其是重登族谱,认祖归宗,更成为心中执念,压过一切。
只是对于形势式微的旁支别脉而言,想要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
倒不是说只有读书考功名这一条路,而是相比之下,这一条路是最有希望达成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家族咬咬牙,能够支撑得起。
陈源叹口气,接着道:“而且你要知道,这次打点的钱,基本都是小郎自己出的。”
陈志不说话,他知道这次要花的钱并不止那些,家里多年的积蓄也一并拿了出来,可以说是孤注一掷。
不过父亲所言有理,家族流落在外,叔伯兄弟间若不抱团,四分五裂的话,只会被外人欺负。莫说返回祖地,便是在乡下都站不住脚。
如果这次事成,陈晋能够进入衙门办差,对于家里自是好事。
他心间仍有不安,忍不住问:“爹,若是对方收了钱,办不成事,岂非鸡飞蛋打?”
陈源呵呵一笑:“不可能的。只要银子送出去了,那就代表着事成。否则的话,传扬出去,赵主薄失信,砸了招牌,以后谁还敢找上门来?”
陈志哦了声,觉得颇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