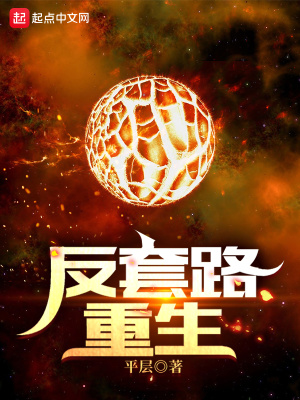三K小说网>刚毅坚卓作文素材 > 第五六九章 书店偶遇(第2页)
第五六九章 书店偶遇(第2页)
其实贺础安早就知道那包袱里是什么东西,从前他每次坐在“中国通史”的课堂里,都会看着钱穆先生拎着这个包袱走上讲台,接着先生便会解开这个布包袱,从里面拿出一沓厚厚的笔记,先生曾经说过,这是他早在四年前在北大讲“中国通史”时就积攒下来的“宝贝”,特意从北平带到了南岳山中,又几经辗转带到了昆明,甚是珍贵。
钱穆先生生怕贺础安吃不饱,给他点了牛肉包子、鸡汤馄饨、荠菜饺子和黄封糕,摆满了一桌子。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钱穆先生问起贺础安学习上的情况,贺础安只觉得自己读书太少,尚未形成体系,不过上个月在报纸上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获得了不少启发。
钱穆先生笑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篇文章的?”
“是陈寅恪先生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他说先生的这篇‘引论’写得极好,是‘一篇大文章’,让我们一定要买来读!我就赶紧跑去报摊买了回来,去晚的同学没有买到,大家就互相借着看。”
贺础安本是十分腼腆的人,可是说起他钟爱的历史来,就不知不觉打开了话匣子:
“这篇‘引论’真的让我深受教诲!诚如先生文中所言,‘治史应当在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如今国家内忧外患,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社会之积弊和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同时展现于国人的眼前,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要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所知,’这正是我们史学人的责任——”
钱穆先生笑着摆了摆手:
“好了好了,你这是把那一篇东西背下来了吗?”
贺础安脸红了:
“看得遍数多了,就不知不觉背下来了。”
“贺础安,你小小年纪能有这种觉悟,实在难得,我一直都很欣赏你,你为人踏实,性子稳,的确是学史的材料,不过眼下这条路可不好走啊!”
贺础安的目光变得坚定了,他直视钱穆先生的双眼,郑重地说道:
“先生说的我都明白,我不怕。先生在‘引论’中还讲到,‘人都有个性,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知晓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个性’所在,然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反之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与事业中,才能了解其个性的特殊点,必须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治国史的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先生,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学史尤其应该做到这一点。三六年我刚考上北大的时候,不过略读了几本史书,便自以为很了解这个国家了,可在这两年里,我去了很多从未去过的地方,也见了很多从未想象过的人事物,我这才意识到,我之前对于这片土地的认识太狭隘了。直到经历了这许多,我才敢说自己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气’,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各种面向。先生,我敢说,我比以前更加坚定自己要走这条路了,我要写出先生所说的‘国史新本’,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的病痛之症候,为有志之士革新现实提供必备的参考。”
钱穆先生露出满意的笑容,不住点头:
“贺础安,你有志于此,我真的很高兴。哎,这还剩了许多啊,你再多吃一点,吃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