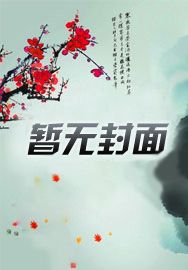三K小说网>靖明农甘肃 > 第104章 既赢了又输了浑身难受为盟主SP宝儿姐加更22(第3页)
第104章 既赢了又输了浑身难受为盟主SP宝儿姐加更22(第3页)
“良知难以轻致,人欲难以尽灭。二位先生之法,以朕观之似乎殊途同归,本质如一,可兼行否?”
话一出口,大战立起。
“非也!”
杨廷和立刻郑重地反驳了:“本质截然不同!致良知之法是未致知而以为可,意未诚心不正则以不修之身行之,则难免家不齐国不治而天下乱。灭人欲之法乃以天理为纲,以礼法为常,未致知者、意未诚者、心未正者亦可明如何修身、如何行事,未臻道境亦不致肆意妄为、祸乱家国。盖天理不因人心而移动,而人心各异。若兼而行之,存天理灭人欲乎?率性且先行而后致良知乎?各执一词,则万民无所适从。”
“予倒不以为然,自可兼行。”
王守仁微笑着进入了状态,杨廷和微微一愣。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兼行?你们心学一脉可是认为心就是天理的!
那还不是我心最大,唯我独尊?
我跟你是反着来的!
杨廷和立即进入了让朱厚熜觉得更懵的状态。
从这一刻开始,他直接开始把本质问题跑出来,这下子什么理、性、心、气、欲、善、恶……各种各样理学心学关于宇宙论与本体论、人性论与心性论、知行观与修养论、天人观与境界论的专业词汇全蹿了出来。
很多字朱厚熜听得懂,但连在一起就不懂了。
做个“学问精深”的皇帝的野心正在摇晃:太难了。
但朱厚熜还真的进入了学习状态,勉强跟随着,研究他们的思维。
暂时听不懂的,回去之后严嵩刘龙可以再帮他复盘、细讲。
理学也好心学也好,它们实际上确实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哲学思想领域的认识。
在内里,它反映着这个时代人的三观。在外表,他也与官学、统治工具密切关联,是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
杨廷和几乎是一开始反驳就火力全开,抓住心学更依赖个人天赋和当前境界的短板穷追猛打。
说到底就是怎么治国的难题:兼而行之,有些人水平不够就先去做,做了之后你就能保证他们会反思进步?没有个统一标准告诉天下人怎么做,那么非礼的、犯法的,还不天下大乱?
对杨廷和的一番长篇大论,王守仁仍旧只是保持了放松的姿态微笑说道:“礼法自不可动,天理昭昭,心虽既理,亦须渐致良知。诸圣先贤教化天下,礼法谁人不知?致良知之法,乃是自不逾矩而始,至明道成圣而终。予言可兼行,乃于克己更进一步,循序渐进自己身良知而守礼、明理。若只知克己、灭人欲,不得致知之法,岂非固守原地,天下士人、百姓尽皆浑浑噩噩、不图精进?”
刻意对心学了解更多一点的朱厚熜听懂了:你理学只求下限,天下人守规矩别捣乱,但这样一来不就会越来越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我说可以兼行,就是你管下限,我来尝试拔高上限。
这杨廷和如何能忍:现在争的就是那些上限的问题!
谁决定了大明的上限?士人啊!哦陛下你先把刀放下,你尊儒,你也是自己人。
继续……你心学来负责拔高上限的部分,就是让让士人舍弃泛观博览这条更稳妥但更难的道路,选择你“我心即理”、“有知即行”、“行后渐成”的捷径路子,放任自己可能不正确的“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良知哪有那么好致?看人的!